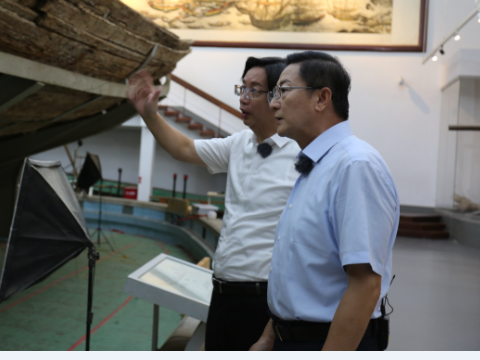楊曾文先生的日本佛教與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發(fā)佈時間:2023-11-21 09:51:39 | 來源: | 責(zé)任編輯:李芳楊曾文先生,1939年出生於山東即墨。1959年入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就讀,1964年畢業(yè)後被分配至中國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佛教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佛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dǎo)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2006年8月,獲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榮譽(yù)學(xué)部委員終身學(xué)術(shù)稱號。
作為中國著名的佛教學(xué)學(xué)者,楊先生常年致力於中日佛教思想、佛教交流史等專業(yè)領(lǐng)域研究,並多次出訪遊學(xué)于海外,[①]既收集佛學(xué)研究珍貴史料,又與外國學(xué)者積極交流。他治學(xué)嚴(yán)謹(jǐn),歷史、文獻(xiàn)、思想三者並重,不僅開拓了國內(nèi)學(xué)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為後世日本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而且積極組織對外交流活動,對中日佛教學(xué)術(shù)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楊先生人格高尚,具有至真至深的家國情懷,以身作則踐行“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其人品、學(xué)品為後輩們樹立了榜樣。
一、研究領(lǐng)域及主要研究成果
楊曾文先生積澱深厚,研究成果斐然。目前已出版《日本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唐五代禪宗史》《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佛教與中日兩國歷史文化》等專著12部,翻譯《日本佛教史綱》(村上專精著)、《印度佛教史概説》(合譯)2部,校編《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臨濟(jì)錄》《神會和尚禪話錄》等佛典語錄5部,主編和參編《佛教文化面面觀》《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等著作15部,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中國凈土宗在日本的傳播和發(fā)展》《鳩摩羅什的“諸法實(shí)相”論》《<六祖壇經(jīng)>諸本的演變和惠能的禪法思想》等284篇,另有譯文36篇、序跋51篇。據(jù)數(shù)據(jù)庫的保守統(tǒng)計,[②]其部分學(xué)術(shù)論文被引達(dá)420次(其中碩博學(xué)術(shù)論文270余次,佔(zhàn)比約65%),[③]著作被引多達(dá)5100余次(其中圖書引用近2700次,佔(zhàn)比52%),[④]足見楊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學(xué)界影響力之大、社會反響之高。楊先生的研究主要涉及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日本佛教研究和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三方面,以下對此做簡要介紹。
(一)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
有關(guān)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的研究,細(xì)分之下又有佛教思想與佛教史研究、禪宗史研究和禪宗文獻(xiàn)研究三者之別。
1.佛教思想與佛教史研究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佛教的起源》(中國建設(shè)出版社,1989;臺北,佛光出版社,1991)、《中國佛教史論》(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2)、《隋唐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4)三部。其中《佛教的起源》以漢譯《阿含經(jīng)》等經(jīng)典為主要資料,考察和論述了佛教的起源和早期發(fā)展,並介紹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教義思想及其在印度的傳播概況。《中國佛教史論》是楊先生於1999—2002年陸續(xù)發(fā)表的20篇學(xué)術(shù)論文總集,內(nèi)容涵蓋了唐五代到宋元時期的禪宗史,也包括一部分佛教學(xué)術(shù)會議專題論文。《隋唐佛教史》則是一部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隋唐佛教的斷代史著作,包括隋唐社會和佛教的關(guān)係、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與發(fā)展兩大部分,書中對唐代道佛之爭、武宗滅佛等唐代佛教的重大問題亦有詳細(xì)考辨和介紹,對於充實(shí)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有著頗為積極的意義。
2.禪宗史研究
楊先生自1994年完成《日本佛教史》《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後,著重開始了中國禪宗史的研究,1999年出版的《唐五代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和2006年出版的《宋元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是該領(lǐng)域的代表作,其中《唐五代禪宗史》出版後頗受讚譽(yù),先後獲第四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2002)、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優(yōu)秀作者獎(2008)、湯用彤學(xué)術(shù)獎(2017),是楊先生在禪宗史研究中當(dāng)之無愧的“扛鼎之作”。該書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論述唐五代禪宗成立和發(fā)展的斷代史專著,揭示了禪宗的産生和迅速興起是佛教適應(yīng)中國社會環(huán)境的民族化進(jìn)程深入的表現(xiàn),在為人們了解唐五代禪宗及其與當(dāng)時社會文化的關(guān)係提供方便的同時,也為從事唐五代歷史、哲學(xué)、宗教、文化等領(lǐng)域研究的學(xué)者提供了參考和借鑒。《宋元禪宗史》同樣是一部斷代史專著,它利用的資料十分廣泛,有正史、編年體史書,還有禪宗語錄、多種“燈史”,也有儒者的文集及碑銘和地方誌、寺志等,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兩宋和元代禪宗的傳播和發(fā)展,對於宋元時期禪宗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禪法思想和著述,以及禪宗與儒、道二教的關(guān)係等均有深入研究。
3.禪宗文獻(xiàn)研究
早在1982年,楊先生利用到日本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研修的機(jī)會,考察了中國佛教傳入日本後的傳播情況,並蒐集以後可能用於佛教研究的資料,將日本學(xué)者整理校勘的敦煌本《六祖壇經(jīng)》和《神會語錄》複製帶回,這成了他以後研究禪宗的起點(diǎn)。在這些珍貴史料的基礎(chǔ)上,楊先生陸續(xù)編校了《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神會和尚禪話錄》(中華書局,1996)和後來的《臨濟(jì)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021年再版),三部內(nèi)典之學(xué)的編校構(gòu)成了楊先生禪宗文獻(xiàn)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以敦煌博物館藏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為底本,參校舊敦煌本和宋代流行的惠昕本而完成的《壇經(jīng)》校勘本;二是附錄,內(nèi)容為發(fā)現(xiàn)于日本大乘寺的宋代惠昕本《壇經(jīng)》及多種有關(guān)慧能與《壇經(jīng)》的重要文獻(xiàn)資料匯集;三是有關(guān)《壇經(jīng)》及其思想的研究論文。《神會和尚禪話錄》以敦煌博物館收藏的寫本為底本,參考胡適及日本鈴木大拙校本編校而成。全書正編收有神會《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dá)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若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等文,附編收錄有關(guān)神會傳記的8種文獻(xiàn),最後是編者所作《神會及其禪法理論》。《臨濟(jì)錄》編校本內(nèi)容有三:一是以《大正藏》本《臨濟(jì)錄》為底本,校之以明版《四家語錄》本、《古尊宿語錄》本的《臨濟(jì)錄》等,對《臨濟(jì)錄》全文進(jìn)行校訂、標(biāo)點(diǎn)和分段;二是附編(一),是從《祖堂集》等佛教史書中選錄的義玄傳記和有關(guān)他禪法的資料彙編;三是附編(二),係編者的研究論文《臨濟(jì)義玄和<臨濟(jì)錄>》,其中對義玄的生平、《臨濟(jì)錄》的編排結(jié)構(gòu)、義玄的禪法思想等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以上三部編校本的編纂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文本校勘—相關(guān)資料彙編—作者生平思想及文本研究”的共通特點(diǎn),對學(xué)界佛教原典文獻(xiàn)的整理有很好的示範(fàn)作用。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楊先生在當(dāng)代佛教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時代價值和世界佛教現(xiàn)狀等方面的研究亦著力甚多,這裡以《當(dāng)代佛教與社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金城出版社,2013)和《當(dāng)代佛教》(東方出版社,1993;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文獻(xiàn)出版社,2004)三部著作為例略加説明。《當(dāng)代佛教與社會》是楊先生擔(dān)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六年間參加學(xué)術(shù)會議所提交的47篇文章的匯總,題材各異,涉獵廣泛,但皆不離當(dāng)代佛教,反映了楊先生對當(dāng)代佛教所面臨的生存和發(fā)展問題的關(guān)心與思考。《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共收錄論文37篇,內(nèi)容包括對當(dāng)代人間佛教基本要求的思考,對中國禪宗的傳統(tǒng)、主要特色及其時代精神的探究,對佛教的回顧與展望,對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考察等,觀點(diǎn)與時俱進(jìn),具有時代精神,同時不減學(xué)術(shù)價值。《當(dāng)代佛教》是一本介紹世界當(dāng)代佛教的科普性著作,介紹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及其發(fā)展,當(dāng)代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佛教及其影響,二戰(zhàn)後日本的佛教及朝鮮、南韓和蒙古、蘇聯(lián)的佛教,歐美的佛教和佛教研究,國際佛教組織和主要活動,佛教節(jié)日和紀(jì)念活動等,其中不乏涉及佛教民族主義、佛教社會主義、新興宗教、佛教改革思潮等國內(nèi)鮮有人提及的新話題,書後還附有二戰(zhàn)後世界佛教大事件年表。該書內(nèi)容詳實(shí),舉證豐富,論述客觀且系統(tǒng),從中可了解到當(dāng)代世界佛教之概貌和發(fā)展趨勢。
(二)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以上簡述了楊先生在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領(lǐng)域的代表作,下面我們以時間線為軸,介紹一下楊先生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領(lǐng)域的研究概況。我們基於相應(yīng)的研究成果,將楊先生對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整理為1964—1972年、1980—1982年、1990—1996年、2013年以後四個時間段,分別對應(yīng)萌芽、開花、結(jié)果和圓熟時期。
1.萌芽期(1964—1972)
如前述,楊先生從事佛學(xué)研究,可追溯至大學(xué)畢業(yè)後被分配至中國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1964年。進(jìn)所工作時,楊先生按照當(dāng)時所裏的學(xué)術(shù)分工開始接觸日本佛教,這成為他此後佛教研究的濫觴。然而,楊先生的學(xué)術(shù)之路並非一路坦途。時值特殊時期,全國的學(xué)術(shù)工作者被迫停頓工作,楊先生也于1969年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全體成員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參加了三年農(nóng)業(yè)勞動。不過,其間楊先生對日語的學(xué)習(xí)未有停頓——一本《毛澤東文選》日文本成為彼時楊先生學(xué)習(xí)的最佳材料。1972年,楊先生從河南幹校回京,接受了黃心川先生的建議,著手翻譯日本近代佛教史學(xué)奠基人之一、佛教史研究先驅(qū)村上專精(1851—1929)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綱》,由此而對研究日本佛教産生了極大興趣並懷有一種使命感。
2.開花期(1980—1982)
1980年,楊先生參加由杜繼文先生任主編的《佛教史》編寫組,負(fù)責(zé)日本及朝鮮佛教部分的撰寫。1982年1月至4月,楊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研修期間,蒐集到日後用於佛教研究的一些資料,這此訪學(xué)經(jīng)歷也成為楊先生研究禪宗的起點(diǎn)。自1982年起,楊先生幾乎每年都抽時間研究日本佛教,並先後發(fā)表多篇論文。[⑤]此期間的代表作有《中國凈土宗及其在日本的傳播和發(fā)展》(《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商務(wù)印書館,1982)、《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初傳期的流傳情況》(《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等。
3.結(jié)果期(1990-1996)
隨著研究的不斷積累和沉澱,楊先生迎來了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的豐收期:1992年,擔(dān)任《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副主編,負(fù)責(zé)主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部分並撰寫詞條;1995年,出版《日本佛教史》;1996年,《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與張大柘、高洪等學(xué)者合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與日本學(xué)者源了圓合編)陸續(xù)問世。此時期重中之重的成果當(dāng)屬《日本佛教史》,楊先生曾言該書是有生以來下功夫最大的一部著作。[⑥]該書自1990年底開始撰寫到1993年完成,歷時三年。1995年出版後一版再版,幾經(jīng)脫銷,廣受學(xué)界好評,深受讀者喜愛。《日本佛教史》是中國第一部日本佛教通史專著,以論述日本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形成為重點(diǎn),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了中國佛教傳入日本1500年來在日本傳播、盛行和發(fā)展的全過程,同時揭示佛教這一文化紐帶在中日兩國源遠(yuǎn)流長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書中內(nèi)容不只關(guān)乎日本佛教,也涉及中日佛教交流史。該書論述精當(dāng),旁徵博引,綜析詳辯,是日本佛教史研究中的經(jīng)典之作,是有志於研究日本佛教、中日文化交流史學(xué)者的入門書與必讀書。
《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是楊先生主編並參寫的著作,書中論述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佛教歷史,在編寫時將佛教置於各個歷史時期加以關(guān)照。就內(nèi)容來看,它對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的歷史、重要人物與事件,佛教在日本對外侵略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戰(zhàn)後日本佛教的重新組合和適應(yīng)時代的改革,當(dāng)代日本佛教的宗派和組織包括新興佛教團(tuán)體,佛教與日本的政治文化關(guān)係,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日本百年來對佛教的研究取得的成績,日本佛教在國外的傳教情況等內(nèi)容都作了比較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為我們了解日本近現(xiàn)代的佛教情況提供了方便。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作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與日本大修館書店合作出版)叢書中的一卷,由楊先生和日本學(xué)者源了圓擔(dān)任主編,中國學(xué)者和日本學(xué)者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撰寫而成,觀察角度不一而同,寫作風(fēng)格各有特色,書中設(shè)置了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道教與日本神道及民間信仰、佛教在日本的傳播、日本佛教的宗派、中日佛教民族化和儒佛關(guān)係、中日兩國基督教的早期傳播、近現(xiàn)代中國與日本的佛教等專題,吸收了中日兩國學(xué)術(shù)界的研究成果,對中日宗教和兩國的宗教交流作了整體性概括。
4.成熟期(2013年至今)
《中華佛教史》是中國第一部佛教通史,由學(xué)界泰斗季羨林、湯一介兩位先生擔(dān)任主編。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楊先生承擔(dān)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的寫作,該書論述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的過程及中日佛教的源流關(guān)係。在該書的自序中,楊先生指出了此書與《日本佛教史》在取材與重點(diǎn)研究內(nèi)容上的五點(diǎn)不同之處:其一,論述以中國佛教為主體;其二,考察以兩國僧人對待中國佛教的著眼點(diǎn)、態(tài)度等為重點(diǎn);其三,揭示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史不同時期的地位與影響;其四,闡述中國佛教對日佛教乃至歷史文化的整體影響;其五,以史實(shí)論述表彰為兩國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貢獻(xiàn)的重要人物。就著作的價值和貢獻(xiàn)而言,《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一方面在學(xué)科建設(shè)上豐富了“中國佛教”外傳史的內(nèi)容,充實(shí)了以往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對中國讀者加深對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了解、增進(jìn)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也大有裨益。
著書立説之外,楊先生利用日語專長還翻譯了多部日語專著和論文,個中佼佼者如《日本佛教史綱》(村上專精著、汪向榮校),此書從時間上來説,屬於楊先生日本佛教研究的入門之作。日文原版分上下兩卷,上卷出版于1898年,下卷出版于1899年,是日本佛教文化研究領(lǐng)域的早期代表作。原作者以提綱掣領(lǐng)的方式揭示了日本佛教史的綱要和主要內(nèi)容,比較考查了日本各個佛教宗派産生和發(fā)展的源流,對所依據(jù)的佛教理論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差別進(jìn)行比較説明,論述了佛教在日本社會和文化發(fā)展史上所做出的貢獻(xiàn),對日本歷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做了概括性的介紹。該書經(jīng)楊先生譯介到國內(nèi)後,由商務(wù)印書館分別於1981年、1992年、2022年推出三版,可見其影響力和重要性。楊先生的其他譯文還有《日本佛教研究現(xiàn)況》(佐佐木教悟,《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明代文化的傳播者——隱元隆琦》(鐮田茂雄,《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日本佛教的特點(diǎn)》(中村元,《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國的凈土變相和敦煌》(中村興二,《中國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等等。
二、研究特點(diǎn)與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
(一)研究特點(diǎn)
縱觀楊先生的學(xué)術(shù)研究生涯,不管是中國佛教史研究,還是日本佛教史研究,早期經(jīng)歷雖有順有逆,中間研究方向有轉(zhuǎn)有變,但自始自終未離佛教研究,想必正是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奠定了楊先生今日的學(xué)術(shù)地位。當(dāng)然,楊先生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研究業(yè)績,更離不開他佛教研究方法論的支援。用楊先生本人的話來説即是“唯物史觀指導(dǎo)下的史論結(jié)合法”,[⑦]換言之,即歷史、文獻(xiàn)、思想三者並重。關(guān)於此,楊先生曾言:“研究任何一個問題,首先應(yīng)理清其歷史脈絡(luò),其次要最大限度獲取、考辨並整理相關(guān)的第一手文獻(xiàn)資料,最後在歷史脈絡(luò)清晰、文獻(xiàn)資料可靠的基礎(chǔ)上嘗試對該問題的思想實(shí)質(zhì)進(jìn)行理論概括。”[⑧]對研究者而言,開展學(xué)術(shù)研究首先要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副清晰的學(xué)術(shù)地圖,有了地圖的指引才能正確尋找到自己想要的研究目標(biāo),然而找到目標(biāo)並不意味著研究到此為止,對目標(biāo)進(jìn)行解讀才是研究者的真正終點(diǎn)。在楊先生的治學(xué)過程中,他始終以研究佛教史為重點(diǎn),史料結(jié)合史識,紮實(shí)文獻(xiàn)功底之下更見透徹的理論分析。具體到日本佛教研究,楊先生的這一“歷史考察+文獻(xiàn)運(yùn)用+理論創(chuàng)新”的治學(xué)方法被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首先,密切結(jié)合中日兩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來考察佛教東傳及在日本的傳播和發(fā)展演變歷程;其次,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佛教文獻(xiàn)與考古資料,同時積極參考和吸收國內(nèi)外的重要研究成果;最後,就佛教傳入日本後的民族化過程、日本古代佛教的特點(diǎn)等問題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創(chuàng)新性觀點(diǎn)。
(二)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
我們説,佛學(xué)研究在中國的宗教學(xué)研究中佔(zhàn)據(jù)著重要地位。楊先生浸淫其間近60年,造詣之深常人難以望其項背。毋庸置疑,楊先生為中國的佛學(xué)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貢獻(xiàn),僅以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而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開拓了國內(nèi)學(xué)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為後來的日本佛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
北京大學(xué)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就曾指出:“真正可以稱得上是漢語寫作的日本佛教通史只有楊曾文教授著于20世紀(jì)90年代的《日本佛教史》。楊著填補(bǔ)了中國學(xué)術(shù)界對日本佛教研究的空白,在學(xué)術(shù)史上佔(zhàn)有重要地位。該書內(nèi)容較為豐富,吸收了村上專精、辻善之助、家永三郎等人的研究成果,作為近二十年來中文寫作的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日本佛教通史,成為與日本研究有關(guān)的各領(lǐng)域?qū)W者的案頭必備之書。”[⑨]
其二,總結(jié)了日本古代佛教的五大特點(diǎn)。日本佛教雖然“移植”自中國,但它在日本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漫長流傳和發(fā)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點(diǎn),這些特色顯然與中國佛教這個母體相異。1992年,由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日中文化交流——新的觀點(diǎn)”研討會在京都召開。楊先生出席併發(fā)表了《日本古代佛教民族特色的形成》一文。文中他將日本古代佛教的特點(diǎn)概況為以下五點(diǎn):①強(qiáng)烈的佛法護(hù)國的觀念;②神佛同體和一致論思想;③鮮明的宗派意識;④盛行唸佛和唱題;⑤顯著的世俗化傾向。楊先生的觀點(diǎn)和論述既簡練又到位,在當(dāng)時乃至此後,都有相當(dāng)?shù)膯l(fā)性。
其三,填補(bǔ)了國內(nèi)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通史類研究著作的空白。歷史上,中國與日本發(fā)生過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這些豐富的史實(shí)本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産出許多專題的、綜合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楊先生之前,由於種種原因,該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國內(nèi)長期缺乏關(guān)注,成果乏善可陳。因此,楊先生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開創(chuàng)性意義。不論是他傾數(shù)年之功完成的《日本佛教史》,還是他佛學(xué)研究步入圓熟境界的《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這些成果之於該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價值、史料價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都毋庸贅言。正是在楊先生的“學(xué)術(shù)開荒”下,國內(nèi)的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才逐漸成為研究焦點(diǎn),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
其四,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漢傳佛教的海外傳播史及東亞佛教文化圈的建構(gòu)過程。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是一個大課題,涉及許多內(nèi)容,它與漢傳佛教的海外傳播、東亞佛教文化圈的構(gòu)建都緊密相關(guān),共同構(gòu)成一個互有關(guān)聯(lián)的有機(jī)整體。用東亞的視角看佛教的東傳,或許更能看清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本質(zhì)。借助楊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們得以對這些問題有更好的理解,從中獲得學(xué)術(shù)思路和研究視野方面的靈感和啟發(fā)。
其五,促進(jìn)了中日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交流。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楊先生便通過翻譯將日本學(xué)界的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學(xué)界,這極大地擴(kuò)充了國內(nèi)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理論,激發(fā)了學(xué)者們的學(xué)術(shù)熱情。從1985年至2003年,楊先生與日本東京大學(xué)的鐮田茂雄、末木文美士教授合作,先後組織了10場兩年一度的“中日佛教學(xué)術(shù)會議”。為表彰楊先生的貢獻(xiàn),1999年日本東洋哲學(xué)研究所將“東洋哲學(xué)學(xué)術(shù)獎”頒發(fā)給了楊先生。此外,楊先生還與日本學(xué)者共同主編叢書、共撰論文,前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就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以上種種,交流頻繁,方式多樣,皆是楊先生為促進(jìn)中日學(xué)界學(xué)術(shù)交流所做之貢獻(xiàn)。
三、結(jié)語:兩點(diǎn)思考
(一)欲做事,先做人
學(xué)者在成為學(xué)者之前,首先是一個普通人,因而學(xué)習(xí)做人是步入學(xué)術(shù)生涯的第一步。楊先生在學(xué)問生涯和平常生活中,無不散發(fā)著人格的魅力,閃耀著智慧的光輝。楊老師曾就自己的人生發(fā)出感言,他説在佛學(xué)研究的路上,日本的牧田諦亮、鐮田茂雄、福永光司等老一輩著名學(xué)者對其幫助不小,自己在與他們交往時,尤其注意保持國格、人格,因而得到了他們的尊重,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⑩]在修身養(yǎng)性方面,楊先生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做“不平常事”,淡迫名利,順乎自然,尊重他人勞動成果,反對急功近利,秉持端正的學(xué)風(fēng)和高尚的學(xué)術(shù)道德。
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還需要強(qiáng)烈的使命感和責(zé)任心來做催化劑。楊先生之所以下定決心撰寫一部中國人自己的《日本佛教史》,即是出於對中國在這方面研究欠缺之現(xiàn)狀的痛心疾首。這種使命感還體現(xiàn)在楊先生深切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中。這一點(diǎn),從其論文集《當(dāng)代佛教與社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有結(jié)合時代對佛教義理的詮釋和發(fā)揮,有對佛教應(yīng)當(dāng)適應(yīng)時代和社會進(jìn)步進(jìn)行變革的思考,還有關(guān)於新時期佛教自身建設(shè)、佛教研究和文教事業(yè),以及佛教如何促進(jìn)社會和諧、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推進(jìn)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等問題的探討,反映了楊先生經(jīng)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
俗語有雲(yún):“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楊先生的學(xué)術(shù)生涯恰是對這句話的最好注解。年逾古稀,不改鑽研之志;孜孜以求,不綴筆耕之勤。近年來,楊先生先後完成並出版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佛教與中日兩國歷史文化》兩部皇皇大作,目前仍執(zhí)筆主編叢書《中國禪宗典籍叢刊》,不辭辛道苦,不止步于前;劈荊斬棘,皓首窮經(jīng),不斷開拓學(xué)術(shù)荒土,真吾輩學(xué)習(xí)之楷模。
(二)如何接著説?
如何繼承楊先生開拓的事業(yè),將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走得更遠(yuǎn)更好,是我們當(dāng)下所應(yīng)重點(diǎn)思考的問題。從楊先生的治學(xué)生涯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四點(diǎn)啟發(fā)。
第一,不斷拓展研究視野。要從東亞甚至全球的視野來研究日本佛教與中日佛教交流史,不斷挖掘新史料,提出有意義的新問題。
第二,不斷充實(shí)與更新研究內(nèi)容。近二十年間,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領(lǐng)域,皆出現(xiàn)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特別是2015年,北京大學(xué)王頌教授出版了《日本佛教》,在材料挖掘、方法運(yùn)用、觀點(diǎn)創(chuàng)新等方面皆有新的突破,可謂是對楊先生《日本佛教史》的繼承與發(fā)揚(yáng)。那麼,在“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領(lǐng)域,我們是否也該在楊先生《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一書的基礎(chǔ)上,推出吸收新成果、利用新史料、運(yùn)用新典範(fàn)進(jìn)行深入系統(tǒng)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呢?這顯然是我們“接著説”時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不斷提升研究方法。如何對日本佛教或中日佛教交流史的重要問題開展深入、細(xì)緻、系統(tǒng)的研究?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借鑒與反思日本及歐美學(xué)界的研究範(fàn)式與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在繼承歷史語言文獻(xiàn)學(xué)、宗教哲學(xué)研究傳統(tǒng)的同時,借助數(shù)字化技術(shù),通過真正意義上的跨學(xué)科研究模式,不斷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準(zhǔn)。
第四,不斷促進(jìn)學(xué)術(shù)交流。對當(dāng)下的學(xué)界來説,在促進(jìn)學(xué)術(shù)交流方面可以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實(shí)現(xiàn)。其一,如楊先生所為,將有學(xué)術(shù)價值的國外研究成果譯介進(jìn)來,同時,我們也要將中國學(xué)者的優(yōu)秀成果介紹出去,實(shí)現(xiàn)中外學(xué)者的平等對話。其二,與國外的機(jī)構(gòu)或個人開展合作研究,如前所述,楊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今天的條件下,這樣的合作更容易實(shí)現(xiàn),以研究道元著稱的日本郡山女子大學(xué)何燕生教授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何教授今年申請到了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的一個關(guān)於禪的語言與翻譯的共同研究課題,參與課題的成員有40余位,除了日本學(xué)者,還有來自歐美及中國的10余位學(xué)者,每兩個月舉行一場研究會,由不同國家的學(xué)者各做一次發(fā)表。我有幸參與其中,深感每次研究會都獲益匪淺。其三,聯(lián)合舉辦學(xué)術(shù)會議。楊先生曾經(jīng)參與組織的“中日佛教學(xué)術(shù)會議”迄今已舉辦了15屆,由中國佛教協(xié)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xié)會聯(lián)合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⑪]至今也召開了5屆,在海內(nèi)外學(xué)界與佛教界影響很大。除了這種大規(guī)模的學(xué)術(shù)活動,我們也可舉辦形式更為靈感多樣的小型合作會議,不斷促進(jìn)海內(nèi)外的學(xué)術(shù)交流。
最後,我們想借楊先生的話做一個簡短的結(jié)語:“任何學(xué)術(shù)研究都有前後學(xué)者之間的連貫繼承性,橫向?qū)W者之間的互補(bǔ)性。我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或過程中,盡可能蒐集並參考國內(nèi)外的有關(guān)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與國內(nèi)外的研究‘接軌’。借此機(jī)會,向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的前輩,向一切在佛教研究中做出貢獻(xiàn)的同仁深表敬意。”[⑫]向前輩學(xué)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江靜,女,浙江桐廬人,浙江大學(xué)博士。現(xiàn)為浙江工商大學(xué)東方語言與哲學(xué)學(xué)院教授、博導(dǎo)、院長兼東亞研究院院長。學(xué)術(shù)兼職包括中國日本史學(xué)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guān)係史學(xué)會常務(wù)理事兼中日關(guān)係史專業(yè)委員會會長、中華日本哲學(xué)會理事、浙江省中日關(guān)係史學(xué)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海外文獻(xiàn)資料中心副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日本千葉大學(xué)客座教授、南韓東國大學(xué)客座研究員。
陳繆,浙江工商大學(xué)東亞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自1982年起,楊先生先後任日本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外國招聘學(xué)者”(1982年1—4月)、日本東京大學(xué)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85年9—12月)、美國康乃爾大學(xué)訪問學(xué)者(1991年4月)、日本京都大學(xué)文學(xué)部“招聘教授”(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日本駒澤大學(xué)研究員(1997年10-12月)。
[②]論文被引情況檢索自中國知網(wǎng)數(shù)據(jù)庫,著作被引情況則檢索自讀秀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引用時間為2022年10月12日。
[③]論文中被引用數(shù)量的前三名為《唐宋文殊菩薩信仰和五臺山》(27次)、《試論東漢時期的豪強(qiáng)地主》(18次,係楊先生的北京大學(xué)畢業(yè)論文)、以及《構(gòu)建和諧社會與宗教的理論審視》《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史論》《鳩摩羅什的“諸法實(shí)相”論》《<六祖壇經(jīng)>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上述四篇論文被引皆16次)。
[④]著作類中被引用數(shù)量的前三名為《唐五代禪宗史》(749次)、《日本佛教史》(584次)、《神會和尚禪話錄》(505次)。
[⑤]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⑥]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⑦]黃奎、楊曾文:《史論結(jié)合,研究佛教歷史》,《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⑧]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⑨]王頌:《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20世紀(j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19頁。
[⑩]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⑪]世界佛教論壇由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佛教界倡議發(fā)起于2005年,旨在為熱愛世界、關(guān)愛生命、護(hù)持佛教、慈悲為懷的有識之士搭建一個平等、多元、開放的高層次對話、交流、合作的長效平臺。
[⑫]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9/5/2023951693879105099_432_3.mp4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9/5/2023951693879105099_432_3.mp4聆聽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迴響︱似是故人來

楊曾文先生的日本佛教與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楊曾文先生,1939年出生於山東即墨。1959年入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就讀,1964年畢業(yè)後被分配至中國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佛教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佛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dǎo)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